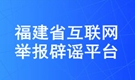|
人们读朱子,研究朱子,特别是系统全面地研究朱子,离不开一部著作,这部著作就是《朱子语类》。 先说说《朱子语类》这部著作是怎么来的。 《朱子语类》的编撰者是朱子的私淑弟子黎靖德,所谓私淑弟子,是指未入其门而得其真传的弟子。黎靖德于南宋景定四年(1263)完成该书编辑,咸淳六年(1270)刻印出版行世。该书共140卷,约250万余字,是一部大著作。主要记录朱子与门人弟子讲学时的问答笔记,也有朱子只说给门人听的语录。《朱子语类》的初始记录时间是乾道六年(1170),到庆元六年(1200)朱子临终前四天止,共收录了大约一万四千二百余条语录。朱子一生从事讲学,门人弟子对他的讲话和答问都有作笔记,朱子辞世后,门人对这些记录进行编辑刊印,前期有多种版本,详略不一。其中主要有南宋嘉定年间李道传辑录朱子门生廖德明等32人所记的,刻印於池州的《池录》;有嘉熙年间李性传辑录朱子门生黄幹等42人所记的,刻印於饶州的《饶录》及门生蔡杭等23人所记,也刻印於饶州的《饶后录》;有咸淳初年吴坚采以上三录所遗漏的4人之记,刻印於建安的《建录》。还有按分类编辑的,有嘉定年间黄士毅所编,刻印於眉州的《蜀本》;有淳佑年间王佖续所编,刻印於徽州的《徽本》。以上五种书称为三录二类,同时流行,由于互有出入,又翻刻不一,讹误由此滋生。后来,黎靖德融汇了以上五种书,对有出入的部分进行整理完善,删去重复的有谬误的语录一千一百五十余条,然后以类归纳编辑成书,名为《语类大全》,也叫《朱子语类》。该书传世后,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。当然,朱子所说的话,也常因时间或对象的不同,及抄录者理解力的不同,还有不少互相矛盾的地方。后世学者对此还作了一些整理完善,如明成化九年(1473)的陈炜刻本、清《四库全书》本,民国胡适的《朱子语类的历史》等,都是对该书详尽考据的代表。 那么,这部大书的内容具体有那些呢? 以卷章来看,该书从第一卷《理气上》到最后一卷《论文下》共140卷。 以类别来看,包含了理气、性理、鬼神、知行、力行、读书、为学之方、训门人、杂类……等26个门类。 从编排次序来看,首论理气、性理、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,强调以太极、理为天地宇宙之本;次论性情气质、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。无非告诉人们有天地然后有人物,有人物然后有性情欲望,而仁义礼智的道理,则是人们把握性情控制欲望的根本。再论知行、力行、读书、为学之方等认识论之法,又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问答语录展开,进一步为前面天地之本性命之原的道理明辩笃行。尤其在训门人中,全面解答了门人的各种问题。对孔子、孟子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邵雍及朱子等均有论述,主要是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来求正前面所说的道理。同时也对老庄佛陀之说展开议论,以异端之说会蒙蔽真理,强调必须予以坚决排斥方能维护好儒家之道统。最后对当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进行议论,旨在说明此理之行于天下与否,乃是治与乱、兴与衰的原因。对那些不可以归类的部分,则用杂类归纳,最后以论文结尾。该书在形式上虽和《论语》相似,都是问答式的语录体,但内容组织上层层推进,逻辑性极强,改变了《论语》在组织形式上结构涣散的弊病。 从内容长短来看,最长的部分是卷第十六《大学三》,共辑录了二百五十三条,讨论《大学》经文;最短的部分是卷第八十八《礼五》,仅录了八条,讨论《大戴礼记》。 内容涉及哲学、自然科学、政治、史学、语言学等方面,体系庞大,析理精密,层层推进,《朱子语类》虽不是朱子所定,但反映了朱子学说的“大要”及基本思想,是研究朱子的重要资料。因书中引用了大量的问答对话语句,语句又大多保留了当时特别是闽北当地的方言,故该书还可以作为语言学的重要资料,用以研究南宋特别是闽北一带的语言。 参与《朱子语类》记录的共有门人弟子一百零一人,其中不知名者四人,同录者三名,所以《语类·序目》所列的《语录姓氏》里有姓名的九十四人。最早开始记录的人是杨方,他是隆兴元年(1163)进士,于乾道六年(1170)开始辑录,那年朱子四十一岁,其学问大旨和经学理论都已成熟,或许也因如此,朱子方才让弟子们开始记录他的语录。最迟记至何年,为谁所录,实际上没有准数,只能推测。门人蔡沈在他的《朱文公梦奠记》中说朱子临终前四天还在和弟子们解说《西铭》,而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有关于《西铭》三十余条,卷一0七有十余条,记录这些条目的人有好几个,所以,最迟记录是否为去世的那年,也只能推测可能是,而为谁而记,就无法确定了。 《朱子语类》以问答形式出现居多。通常门人有问,朱子即予回答。这点也教为有力地反驳了某些西方学者丑化中国古代教育“只说教,不互动问答”的偏见。事实是,朱子特别重视学生发问,他曾经不满意学生的不提问:“近来全无所问,是在此做甚工夫?”朱子回答学生提问因人而异,或厉声回答,或立刻回答,或良久回答,或笑而不答,但都极为亲切。《朱子语类》在这方面,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模式和特色的样板。 对《朱子语类》于后人的作用,用朱子本人在编辑程颐语录时的观点:“伊川在,何必观;伊川亡,则不可不观矣。”朱子语录的价值,亦可作如是观。 |
- 分享到:




2、本网未注明“来源:建瓯新闻网”的文/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,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。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,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“来源”,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。如擅自篡改为“来源:建瓯新闻网”,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。如对文章内容有疑议,请及时与我们联系。
- ICP备案:闽ICP备2022017649号 闽公网安备35078302000127号 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备案[20141202]号
- 主办单位:建瓯市委宣传部 承办单位:建瓯市融媒体中心
-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号:35120210018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:113420055
- 建瓯新闻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0599-3725806 举报邮箱:joswwxb@126.com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:0591-87275327
- 邮编:353100 站长统计 网站维护:东南网
- 建瓯新闻网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或建立镜像